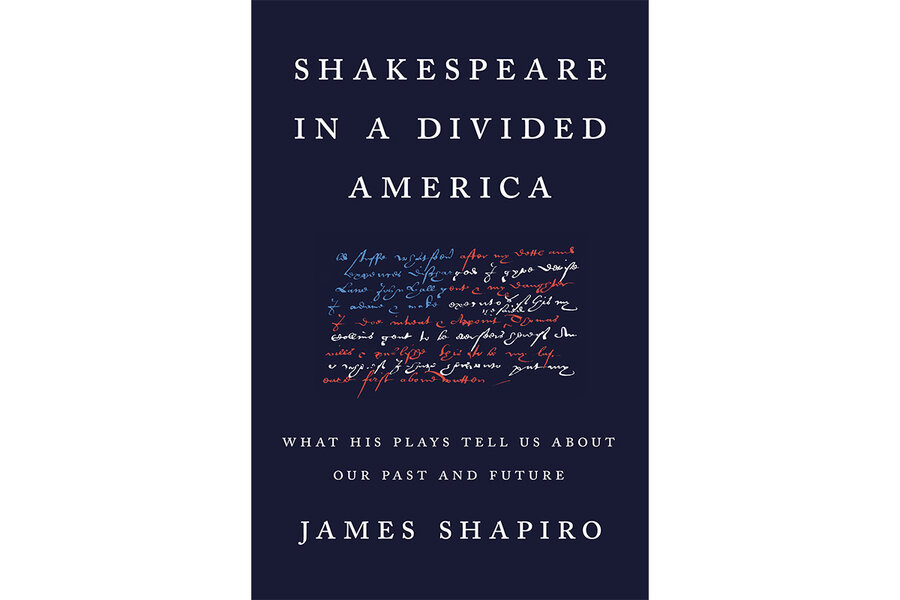
James Shapiro, Shakespeare in a Divided America, London: Faber & Faber, March 2020, 320pp
一个幽灵,英国文学的幽灵,在美国游荡。当“五月花号”的朝圣者抵达科德角时,他在斯特拉福德已去世四年。莎士比亚肯定没有料想到,他的戏剧将会和《钦定本圣经》一道在新大陆被无数人诵读,他塑造的角色将会在更辽阔的国土上经历意想不到的变形和复活。他也不会预见在未来四百年间,美国人民都借助他、利用他、通过他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或焦虑,而无数的纷争和冲突,也将借他的戏剧被揭示和激化。当美国经历一轮又一轮撕裂之时,莎士比亚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一样阴魂不散,不断归来。
专攻莎士比亚的著名学者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在2020年出版了《莎士比亚在分裂的美国》(Shakespeare in a Divided America)一书。他选取美国历史上八个重要时刻,讨论特定年代上演的某部莎剧、或者与莎剧表演相关的事件所引发的全国争议。八个案例中,四例发生在十九世纪,三例在二十世纪,最新、也是最劲爆的事件就发生在2017年的纽约。这本书可视为莎剧在美国历史重要节点的接受史和影响史,也是透过莎剧的棱镜所观察到的美国史。
民要攻打民
仅看莎剧所涉及主题之多、之广,的确称得上“俗世圣经”(secular scripture)。因其包罗万象,随时可与任何时代发生摩擦和碰撞。我们暂且抛开比如篡位、弑君、废立这些永远循环的宫廷主题不论,莎剧在令现代人异常焦虑的那些主题里,都预先布下了很多珍珑棋局,留待后人破解。一个肤色黝黑的摩尔人和一位白人少女成婚,之后又将妻子杀死,这样的剧情如何让历史上的种族主义者消化?一位丈夫不让新婚妻子吃饭、喝水,像“熬鹰”一样驯服了凶悍的“泼妇”,女权主义者又会如何评论如此野蛮的父权压制?当公爵差遣女扮男装的维奥拉向自己心爱的姑娘求婚,而被求婚的姑娘反而爱上着男装的女主,这种巧妙的身份错乱和性别颠倒,算不算预先碰触到现代人对易装和性别边界模糊的兴趣?当外来者占据荒岛,凭借西洋魔法征服了本岛土著,倡导殖民和反对移民的人士会不会得到新的灵感?而最终被遗弃的卡利班(Caliban),会不会成为塔利班?
书中所讨论的纷争,有些源于莎剧的主题以及意识形态解读,有些则是因莎剧的上演而引发的社会动荡。比如第一章叙述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对《奥赛罗》一剧所发表的政治极其不正确的评论。亚当斯曾担任美国第六任总统,是一位博学而审慎的政治家。1833年,英国年轻的女演员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在美巡演,来到波士顿,在一次饭局中与已卸任总统的亚当斯相遇。二人谈到《奥赛罗》,亚当斯忽出惊人之语,令肯布尔小姐错愕不已,不知如何应对。后来,肯布尔将巡演期间所写的日记发表,其中就包括这场尴尬的对话,但她隐去了亚当斯的名字。不过,此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坊间流传已久。亚当斯情急之下,连续刊发两篇文章,申说自己的主张。其核心观点为,苔丝德蒙娜违背父亲意愿,与摩尔人私下成婚,这样的婚姻“有违自然之理”(a viola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而她悲惨的结局也是自我造成的。夏皮罗教授施展他深厚的文献考索功夫,穷原竟委,将亚当斯对异族通婚的深刻恐惧一直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以及他母亲所作的相似评论。《奥赛罗》是最撕裂美国的莎剧之一,曾反复引爆过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的争论。夏皮罗教授在2024年曾透露,未来将专门为奥赛罗这个虚构人物立传,届时我们将会搭乘“奥赛罗号”街车再次穿行于美国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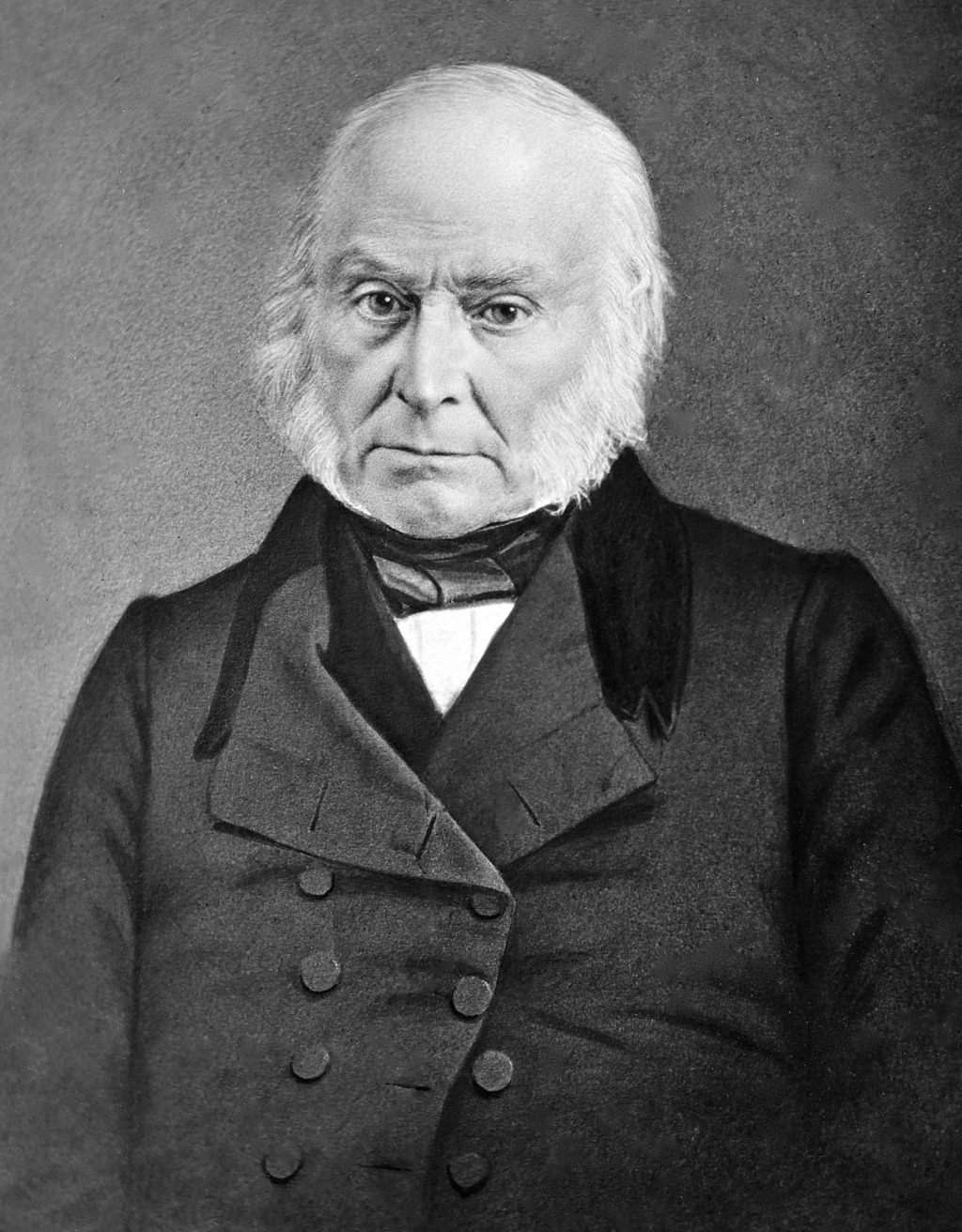
约翰·昆西·亚当斯
因莎剧上演而造成的纷争、甚至流血冲突,最血腥的例子见第三章。冲突的起源本是演员之间的私人恩怨。美国演员曾给英国某名角喝倒彩,二人因此结仇。1849年,英国演员在纽约演出,他的美国对手故意在相邻的剧院大唱对台戏,甚至故意上演相同的戏码。后来,美国演员的支持者雇了五百打手,去英国演员的戏院砸场子,高喊打倒英国人、反对废奴主义的口号。就这样,英美莎剧演员之间的私怨,被掺入当时各种热议的政治议题,升格为穷人与富人的阶级矛盾、扬基佬与约翰牛之间的国家冲突。1849年5月,演艺界的摩擦演变为骚乱,上万人在街头聚集,纽约警察最终开枪镇压,导致二十余人被射杀。这可能是历史上死亡率最高的莎剧演出。
刺向唐纳德·恺撒的剑
在主题和表演这两个层面能同时制造全国范围的撕裂,是八年前的一场莎剧演出。
夏皮罗教授在前言中坦言,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加深了他对莎剧在美国接受史这个主题的兴趣。也就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不久,一场由莎剧而引发的舆论海啸席卷美国。2017年6月,导演奥斯卡·尤斯蒂斯(Oskar Eustis)执导的《尤里乌斯·恺撒》在纽约中央公园上演。尤斯蒂斯在特朗普当选一个月之后,便立即决定排演这出以刺杀独裁者、保卫共和制而闻名的传统大戏,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剧中的恺撒,完全按照特朗普的形象塑造:金发,穿西服,戴红色或蓝色长领带。恺撒做着特朗普的习惯手势,说着特朗普被媒体曝光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语句,就连恺撒妻子说话也带有让人浮想联翩的东欧口音。一切设计都在助推“恺撒=特朗普”的联想。当这个被强烈“特朗普化”的罗马领袖倒在舞台的血泊中,当政治暗杀被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美国观众眼前,1599年的莎士比亚就已暗中返回2017年的美国。

《尤里乌斯·恺撒》剧照
在中央公园版的《尤里乌斯·恺撒》正式上演之前,一位共和党籍的多媒体公司销售经理观看了此剧的预演,对刺杀一场感到强烈不适。消息传出,一片哗然。有人偷录了彩排的视频,只截取刺杀一场的十几秒,在网上四处散播。右翼媒体闻风而动,大肆报道,甚至写出极其耸人听闻的标题,比如《中央公园上演〈尤里乌斯·恺撒〉:“特朗普”遇刺身亡》。特朗普的拥趸当然无暇去注意标题中的引号,只会看到“遇刺”。一时舆情汹汹,右翼人士旋即发动大规模网络进攻和骂战,剧院的赞助商如达美航空公司、美国银行被迫撤销资助,剧院、导演和演员都收到威胁的邮件,甚至尤斯蒂斯的妻子和女儿也收到死亡威胁。
2017年6月16日首演当晚,纽约警方出动警力,维持现场秩序。演到刺杀一场,当剧中的刺杀者喊出“暴政已死”这句台词时,一位年轻女子突然冲到台口,高呼口号,以示抗议,随后被警察带离现场。后续演出基本正常,但这出恺撒剧所造成的全美意见的撕裂,已充分说明在特殊时刻上演《尤里乌斯·恺撒》会传达何等危险的信息。当一个从服饰到言谈都酷似特朗普的恺撒,被当代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刺死在纽约的舞台上,经过这样处理的莎剧,是否已变成诛杀暴君的政治鼓动?这出剧是否应更名为《唐纳德·恺撒》或者《尤里乌斯·特朗普》?这一版的《尤里乌斯·恺撒》已不再是“政治影射”,因为影射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隐微而曲折的表现,但如今,罗马的恺撒已经明晃晃、赤裸裸地对应着美国当年的民选总统。
我们不要忘了,刺杀林肯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1838-1865)在事先准备的书面声明中,已然以布鲁图斯自况,坚信自己的刺杀就是在复刻古代的义举。夏皮罗教授在书中还引用布斯1865年在被追击途中所记的日记:“我像狗一样被围猎,穿过沼泽和树林,所有人与我为敌,我陷入绝望。为什么?因为我做了布鲁图斯为人所敬重之事。”林肯遇刺之后,当时就有人讨论,在美国社会最撕裂的时刻,当一半国人在攻打另一半国人时,以刺杀独裁者为主题的这出恺撒剧,是否给了凶手精神上的指引和行动的驱动力。
夏皮罗作为顾问,深度参与了这出恺撒剧的制作和排演,所以完全支持导演尤斯蒂斯。他指出,导演事先安排了演员潜伏在观众席。在刺杀发生后,当密谋者将手和剑都浸在恺撒的鲜血中时,这些演员会突然站起来,对眼前发生的血腥行为表达不满。导演的意图,在于引导观众注意对政治刺杀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仔细分析,扮作普通观众的演员对政治暴力发出“自发”、零星的谴责,与导演精心设计的多角度、多层面的对特朗普的指涉,是否能构成相反意见之间等量、等价、对等的交锋和抗衡?这是我觉得这一事件还需要更深入分析的问题。
莎士比亚降临美国
《莎士比亚在分裂的美国》一书在讲述美国历史上八次纷争时,还穿插了几个意味深长的轶事,都可以显示美国人民对莎士比亚的态度。在南北战争期间,有位记者制作了一则真的“假新闻”,称一位爱德华·赫尔顿先生(Edward Heldon)从英国移民美国,定居在弗吉尼亚州,在莎士比亚去世两年后的1618年离世。据称,赫尔顿的墓碑上记载,他是莎士比亚的老友,甚至在莎士比亚的葬礼上为诗人抬棺。有好事者遂发起“寻找神秘的抬棺人”活动。夏皮罗教授认为,这个传说的形成和流传,是要在诗人和美国之间强行建立一种实在的关联,而不仅仅是文学的传承(219页)。若展开说,假如莎士比亚的精神遗产仅仅通过文字载体进入美国,这在很多人看来,依然是一种“弱连接”。但如果莎翁的生前好友、曾为他抬棺的“铁哥们儿”竟然在诗人去世不久就亲身来到美国,则莎士比亚的灵魂就仿佛借助朋友的躯壳“亲临”了美国,那么莎士比亚与美国的纽带就不是纯粹精神上的交流,而变得实实在在、甚至有血有肉。
另一则故事,讲述美国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1850-1924)将莎士比亚“国有化”的努力。洛奇在1895年发表《莎士比亚的美国英语》(“Shakespeare’s Americanisms”)一文,夏皮罗教授为《美国文库》(The Library of America)选编的资料集《莎士比亚在美国》(Shakespeare in America, 2015)已收录。英国人对“美式英语”一直非常蔑视,斥之为下里巴人的英语,绝非正宗。洛奇则设法为美国英语找到更早、更深的合法性。他的观点是,当英国人在十七世纪早期于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建立最早的殖民地之时,定居者乃是莎士比亚的同代人,他们所说的英语正是莎剧的英语。莎士比亚使用的大量词语和表达,随着朝圣者横穿大西洋,被移植到新大陆。定居者在陌生土地上建立家园,势必珍视从母国带出的文化宝藏,精心看护。时光推移,英国本土的英语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不知不觉中已败坏了莎士比亚那种强健、元气淋漓的语言。相反,美国人民世世代代都在精心看护第一批定居者所带来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因此反倒保存了更纯正、更接近莎士比亚的英语。按洛奇的理解,英国作为文化宗主国,已然背离了莎士比亚的英文。而美国作为文化的附庸和支脉,反而凭借对莎剧语言的忠贞和监护,晋升为英文的正统。正如成语所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洛奇此文以莎士比亚为武器,以巧妙的方式用“美式英语”压倒“英式英语”,正显示了美国人民想把莎士比亚作为文化资产充分占有、将莎士比亚最大程度“美国化”的努力。
夏皮罗教授在全书最后一章分析了1998年上映的电影《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其中部分内容又与莎士比亚降临美国有关。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甚至摘取了第七十一届奥斯卡电影大赛的多项金牌,但最终上映的版本与1988年最初创作的剧本已相差很远,历经多重的编辑和修改,为了迁就1990年代的美国主流价值。女主角原来的设定更加激烈、放纵、不拘礼法,而且她女扮男装之后与莎士比亚擦出的同性情感火花也更加“擦边儿”。原剧本后来交与著名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来修改。影片结尾,与莎士比亚相恋的维奥拉,最终依旧与女王的宠臣成婚,随丈夫乘船前往美国的种植园。莎士比亚目送女友远去,便开始以维奥拉为主人公,创作《第十二夜》。莎剧中的维奥拉遇海难,被抛到陌生的国度伊利里亚。而电影中“真实”的维奥拉同样遭遇海难,被冲到纽约的海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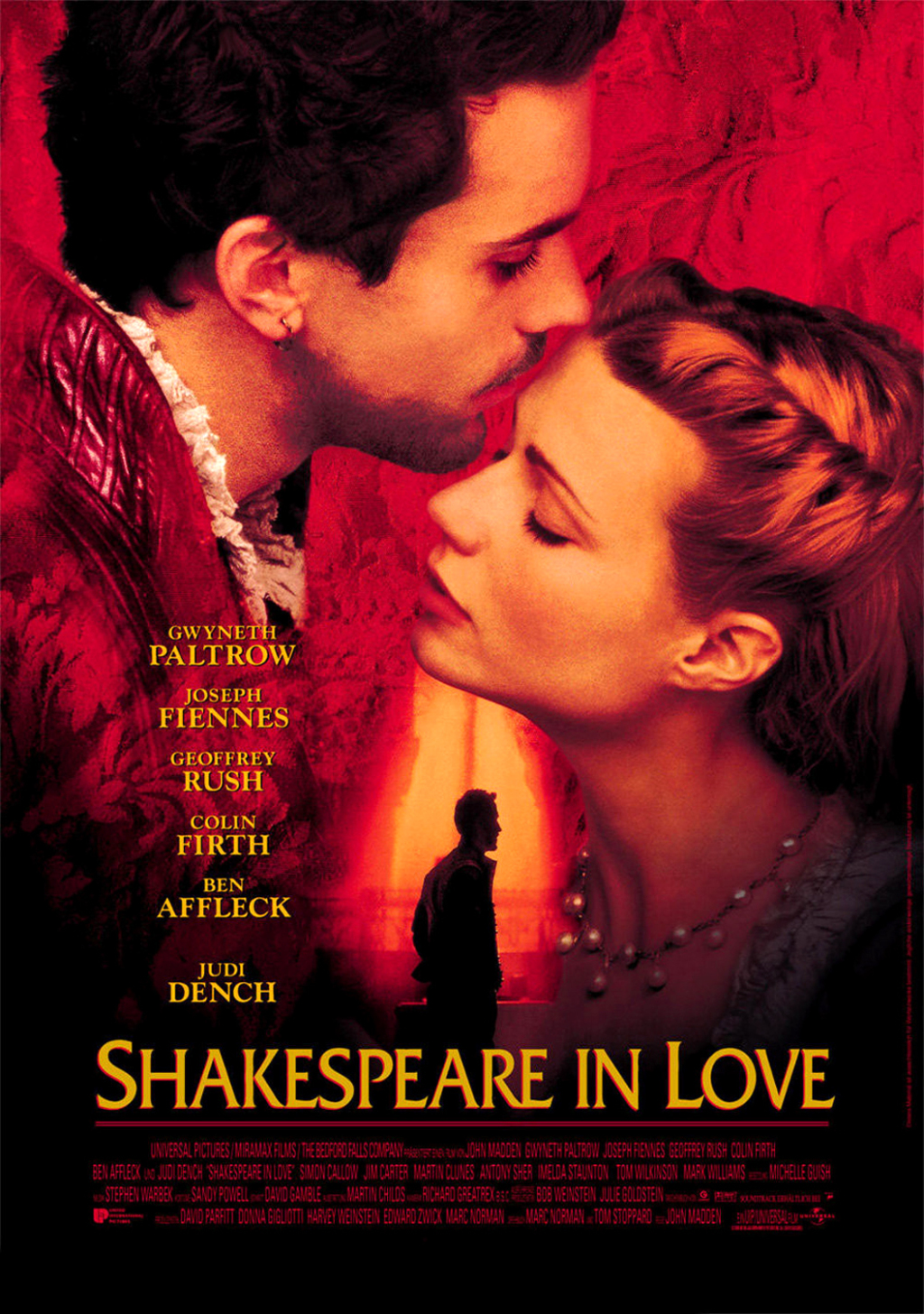
《莎翁情史》海报
在未被拍摄的一版结尾中,奥维拉在海滩遇到两位北美原住民,一人是印第安人,另一人看上去像是黑人。这样的情节当然不会被采纳,因为会唤起观众有关美国起源的尴尬联想。此后,镜头追随奥维拉走向内陆,也就是走进美国历史。她走向的地方逐渐幻化为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甚至包括1998年尚屹立的世贸中心双子塔。这一版最终被舍弃的尾声,经夏皮罗的钩沉,让我们看到将莎士比亚“美国化”的持续努力,一直贯穿到二十世纪末。根据斯托帕德的设计,莎剧人物在莎士比亚生前便抵达美国,如此一来,莎士比亚与美国的纽带甚至早于北美殖民地的建立。维奥拉既是莎士比亚的情人(灵与肉的伴侣),又是莎士比亚创造的角色(文学意义上的后裔),她与莎士比亚的亲密程度当然要远胜过虚构的抬棺人了。这就是一位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国作家以艺术和想象的方式,替美国人民和美国电影公司向莎士比亚宣示主权。
夏皮罗教授书中闪现的这些轶事,都显示美国人民一直以各种方式将莎士比亚据为己有。对美国来说,莎士比亚的影响必须以可感可触、“物质”的方式进入美国,他必须像电影《降临》中的外星人一样实实在在地降临在美国。
“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句话不出自莎剧,但可借来形容莎士比亚给美国带来的分裂。夏皮罗教授的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美国人围绕他们最关切的议题而展开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争吵、争斗、甚至争战,简直就是一部围绕莎剧而发生的美国分裂史。借助这部精彩的著作,我们不仅可以穿越美国史上的纷争来读懂莎剧,同时又可以透过莎剧来读懂美国。我们可以感到,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最深的恐惧、最撕心裂肺的痛苦、最隐秘的创伤和焦虑、最无法调和的分歧和撕裂,往往都借助莎剧得以表达。




